
1. 失踪
2014年3月8日凌晨12点42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200ER从吉隆坡起飞航向北京,一路向35,000英尺的指定巡航高度爬升。马来西亚航空代号为MH,航班号为370。27岁的副驾法里克·哈米德正在驾驶飞机。
那一刻,飞机本该已经降落在北京。
马航370的谜团一直是持续调查的焦点。如此装备着现代仪表和冗余通讯系统的复杂机器居然会完全消失,实在匪夷所思。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想要永久删除一封电子邮件都非常难;想要切断一切现代通讯设施更是难上加难。波音777的设计本就是要保证飞机时刻在线。飞机的消失引发了许多猜测,其中有很多荒谬不经。这些猜测都貌似有理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现如今,一架民航客机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然而这一架确实就这样消失了。八年多以后,它的确切下落仍然未知。
2. 海滩排查者
在飞机失踪后的那天晚上,一位名叫布莱恩·吉布森(Blaine Gibson)的中年美国男子正坐在已故母亲在加州卡梅尔的家中,清理她的遗物遗产,准备卖掉她的房子。此时,他听到了CNN播报的马航370失踪新闻。
吉布森是独子。他的母亲喜欢国际旅行,经常带着他。他七岁的时候决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游历全世界每个国家至少一次。但他一直坚持这个目标,并因此放弃了所有发展固定职业的机会,靠着不多的遗产度日。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一路上浅探了一些很有名的世界奥秘——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丛林中玛雅文明结束之谜,西伯利亚东部的通古斯陨星爆炸,还有隐藏在埃塞俄比亚山中的诺亚方舟遗址。他名片上写着——冒险家。探险家。真相探寻者。他像印第安纳琼斯一样,带着一顶浅顶软呢帽。马航370的消失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第一个值——也是比较准确的一个——被称为突发传输时间差(burst-timing offset),或“距离值”。它衡量信号发射到飞机又传回的时间,并能据此推算出飞机到卫星的距离。它定位的不是单个位置,而是一个近圆内所有可能的等距位置。考虑到马航370的范围限制,近圆可以精确到一个弧形。最重要的弧线是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来自飞机和卫星最后一次握手,与燃料耗尽和主发动机故障等可能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七弧从北部的中亚开始,一路延伸到南部的南极洲附近;马航370于吉隆坡时间早上8点19分穿过这个弧线。可能的飞行路径与第七个弧线的交点就是航线的终点;如果飞机转向北方,那么终点就在哈萨克斯坦;如果转向南方则落在了南印度洋。
技术分析可以基本确定飞机向南飞了。我们从Inmarsat记录的第二个值——突发传输频率差——得知这点。为了简单起见,我将这个值称为“多普勒值”,因为它包含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计量:高速运动物体相对于卫星位置的多普勒频移。这个值自然而然成为飞机卫星通信的一部分。卫星通讯要起作用,必须通过机载系统预测、补偿多普勒频移。
六小时后,多普勒数据显示飞机开始陡峭下降,比正常下降速度快五倍。在穿过第七弧的一两分钟内,飞机扎入海中;撞击海面之前可能已经被撕裂。按这个数据判断,这不是有人工控制的水面迫降。飞机应该已经瞬间碎成千万片了。但没有人知道入海点在哪里,更不用说掉入海中的原因了。而且当时也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能够印证这些解读。
马航370失踪后不到一个星期,可能在高空停留了数小时。
2009年,法航447从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途中在大西洋上坠毁;虽然搜救人员知道确切的坠机位置,黑匣子也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
虽然马方名义上负责整个调查,但他们缺乏进行海底搜救工作的手段和专业知识;澳大利亚作为优秀的国际公民于是牵头调查。卫星数据指向的印度洋地区处在珀斯市西南约1,200英里;海水很深,从未有人探索过;海底蔓延着黑沉沉的、从未被光线触摸过的洋脊。第一个挑战就是绘制全面的海底地形图,以便侧扫声纳机械能够被安全地牵引到水面下几英里。
吉布森离开纪念活动后下决心着手帮助填补他觉察到的一个空缺——沿着海岸搜寻飞机残骸。这将成为他的专攻。他将以私人身份成为马航370的海滩排查者。澳方和马方的官方调查人员都在大力投入水下搜寻。如果得知了吉布森此时的雄心壮志,他们估计会嘲讽他:海滩与海滩之间相距数百英里,残骸碎片从何找起?
3. 母矿
印度洋日日夜夜冲刷着大大小小的岛屿,海岸线绵延数万英里。布莱恩·吉布森刚刚开始寻找碎片时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他第一步先飞到了缅甸——反正缅甸本来就在他的游历计划之中——然后到海边问当地村民飞机碎片在什么地方最容易被冲刷上岸。他们给他指了几个海滩;一个渔民开船把他带过去。他发现了一些碎片,但都不是飞机上的。他让村民们留意飞机残骸,并留下了联系电话,之后继续走访下一站。他走访了马尔代夫、罗德里格斯和毛里求斯,都一无所获。2015年7月29日——在飞机失踪后大约16个月,法国留尼旺岛上的一个市政海滩清洁队遇到了一块大约六英尺长的撕裂翼片,看起来像刚刚被冲上岸。
吉布森飞往留尼旺,在海滩上找到了约翰尼·贝格。贝格很友好;他带吉布森去了找到襟副翼的地方。吉布森四处转了转,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其它碎片,但没有很高的预期,因为法国已经进行了后续搜索,毫无结果。在南半球低纬度,残骸从东到西漂过印度洋需要一段时间。襟副翼可能比其它碎片漂得更快,因为它的一部分可以从水面上支出来,充当一个帆的角色。
留尼旺一家报纸采访吉布森,发了一篇关于这位来自美国的独立调查者的报道。采访时吉布森穿着“继续搜索”的T恤衫。之后他飞往澳大利亚,与两位海洋学家见面会谈,一位是西澳大利亚大学珀斯分校的查里塔·帕蒂亚拉奇,另一位是在霍巴特一家政府研究中心工作,并被安排到主导马航370搜索的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提供指导建议的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这两人都是印度洋洋流和季风的专家,尤其是格里芬,有着多年的追踪海洋漂流浮标的经验,并且还开展了一项研究,来给已寻找到的这片襟副翼漂向留尼旺旅途中的洋流特性建模,希望能够回推它的起点,从而缩小海底搜索的地理范围。相比之下吉布森的请求容易多了:他只是想知道残骸碎片最有可能在哪些位置冲上岸。
吉布森选择前往莫桑比克是因为他还没有去过那里,能够顺手把它算作他到访的第177个国家。他选择了一个叫做维兰库卢什的小城,那里看起来安全,而且海滩很不错。吉布森在2016年2月到达了那里。他记得当时他找当地渔民求教,得知岸礁外一处叫做帕鲁玛的沙洲。渔民们常到这个沙洲去收集从印度洋冲上岸的渔网和浮标。吉布森雇了一位名叫苏莱曼的船夫带他去帕鲁玛。起初,他们找到各种各样的垃圾,大多数是塑料。忽然,苏莱曼把吉布森叫过去,举着一块大约两英尺宽的灰色三角形碎片问:“这是370吗?”这个碎片是蜂窝结构,并在一面上有钢印的“禁止踩踏”字样。吉布森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可能是大型飞机机身上的。
2016年6月,吉布森把注意力转向了马达加斯加偏远的东北海岸。吉布森说他第一天就找到三块碎片,几天后又找到两块。一星期后,在八英里外的一处海滩,又有人送来三块碎片。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人们都知道了他会花钱买马航370的碎片。他说有一次他付40美元买了一块碎片,整个村子狂欢畅饮了一整天。看来当地的朗姆酒很便宜。
不过,在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还是无法从这些冲上岸的碎片往回推导出南印度洋范围内具体的坠海地点。吉布森发现的众多细小碎片确认了信号分析的结论是正确的,那就是失联飞机在继续飞行了六个小时之后,航程骤然终结。没有任何人试图让飞机平稳降落;它粉身碎骨。不过吉布森仍然认为有可能找到类似漂流瓶的物件,比如飞机某个乘客在最后时刻的绝望笔记。在海滩上,吉布森找到几个背包和很多随身小包,但全都是空的。
4. 阴谋论
一位一直密切关注马航370调查的观察家评论道,“很明显马来西亚的首要目标就是把这件事糊弄过去。从一开始他们就本能地拒绝开放透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深藏不能见人的秘密,而是他们不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所以害怕会调查出什么东西让自己难堪。他们是在掩盖什么吗?是的。他们在掩盖那些未知数。”
最后这个调查组按照Annex 13的要求勉强炮制了一份495页的报告,里面塞入了很多波音777系统样板式的描述,明显是从飞机说明书里抄过来的,没有任何技术价值。事实上报告里没有任何内容有任何技术价值,因为澳大利亚主导的调查出具的报告早已完整涵盖了相关卫星信息和洋流分析。
这样的结论招致了无休止的揣测,很多都没有任何根据。卫星数据提供了飞行路线的最好证据,很难反驳,但人们得足够信任数据才能接受这些证据。许多人提出各种说法,并被社交媒体放大,但它们全都无视了卫星数据,其中一些同时还与雷达轨迹、飞机系统、空管记录、飞行物理学、地表曲面理论相左。比如,一位笔名叫做 “毒舌女水手”以塔罗牌占卜为业的英国女博主,事发时正在南亚与她的丈夫和宠犬在大洋乘帆船游荡。她说,在马航370消失那天晚上,他们在安达曼海域。她看到一个形似物体向自己飞来。随后导弹变化成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驾驶舱很亮,飞机被奇怪的橙色光芒所笼罩,拖着一条烟尾。
5. 可能性
其实关于马航370的结局的很多细节都已确凿。首先,飞机的失踪是有意为之。目前已知的飞行路线,加上无线电电子静默,不可能是由系统故障或人为失误造成的。计算机出错、控制系统失灵、飑线、冰、雷击、鸟击、陨石、火山灰、机械故障、传感器故障、仪器故障、无线电故障、电路故障、火灾、烟雾或者神迹,这些都无法解释其飞行线路。
到飞机从二次加强应答雷达视野里消失的时候,由于两位飞行员不太可能协同行动,很可能其中一位已经死亡或失去行动能力、或者被锁在驾驶舱外。军方与民航的初级雷达记录都表明当时马航370的操纵者一定已经关闭了自动驾驶系统,因为飞机向西南的转向非常急,只可能通过手动操作来实现。
科罗拉多博尔德的一位电气工程师迈克·埃克斯纳是独立调查小组一位贡献突出的成员。他深入研究了雷达数据。他认为飞机在转向时已经爬升到了40000英尺高度,接近了其飞行高度极限。
为了能够继续无干扰飞行数小时,制服机舱里不驯服的乘客的一个明显的方法就是故意给飞机减压;或许这也是唯一的方法。在机舱里,如果不是氧气面罩突然落下或者乘务员在使用类似的便携式供氧装置,乘客们可能都不会注意到机舱正在失压。机舱的这些氧气面罩只是为飞机紧急坠落到13000英尺以下时设计的,可使用时间不过15分钟;对40000英尺高空巡航的状况,它们完全没有用。机舱里的乘客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失去知觉,然后平静地死去,不会出现呛气或者急喘。当时的场景大概是这样的:在紧急照明灯昏暗的灯光里,死去的乘客系着安全带坐在座位里,脸上覆盖着从天花板垂下的无用的氧气面罩。
而与此不同的是,驾驶舱配备有四个加压氧气面罩,可以供氧数小时。给飞机减压的人只需要随手给自己戴上一个面罩就可以不受影响。飞机飞得很快。在初级雷达上它只是一个以每小时近600英里速度接近槟岛的不明光点。距离最近的大陆上座落着巴特沃斯空军基地,驻扎着马来西亚的一个F-18截击机中队,还有一个防空雷达,但当时并没有人注意观测。
凌晨1:52,转向后半小时,马航370从槟岛南边飞过,向右大转弯,然后向西北飞经马六甲海峡。飞机转弯时,下方的信号塔记录下了副机长的手机信号。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连接,没有任何内容传输。11分钟后,马来西亚航空调度员以为马航370仍在南中国海上空,并发送了一条短信指示飞行员与胡志明市的空中交通控制中心联系。该讯息无人应答。在飞经马六甲海洋的过程中,飞机仍有人手动驾驶。据前面所述的推测,此时机舱内的所有人都应该已经死亡。凌晨2:22,马来西亚空军雷达捕捉到了飞机最后的一瞥。此时这架飞机位于槟城西北230英里处,正向西北高速飞入安达曼海域。
三分钟后,凌晨2:25,飞机的卫星通讯箱突然重新开始运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整机电力系统被重新启动,同时机舱内也被重新加压。重新启动后,卫星通讯箱向Inmarsat发送了一个登录请求;地面站做出回应,完成了初次连接。如此,地面站记录下了飞机相应的距离和多普勒值,而驾驶舱内任何人对此毫不知情。人们后来恰恰是根据这些信息得以构建出第一弧。几分钟后,调度员给飞机打了个电话。卫星接收到了这一连接,但电话无人接听。一个相应的多普勒值显示飞机当时刚刚向南大转弯。发生这一事件的地点被调查人员称为“最后的大转弯”。这一位置对此后的所有搜寻工作都至关重要,但却始终无法被精准确定。印尼的防空雷达本应显示出具体地点,但当夜该雷达似乎被关掉了。
这时马航370很有可能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向南巡航,飞入夜幕。
6. 机长
在马航370事件中,很难将副机长视为凶手。他年轻乐观,据说正在准备结婚。他没有招惹过任何麻烦,也没有遭人异议或怀疑的记录。他并非是式微的廉价航空公司里工资很低、社会地位更低的德国飞行员。他驾驶着一架闪耀的波音777;在马来西亚,国家级航空公司和其飞行员依然备受尊敬。
让人怀疑的是机长扎哈里。第一个预警信号是官方报告中将他描绘为一个无可指摘的人——优秀的飞行员,平和的居家男子,喜欢玩飞行模拟器。这是扎哈里家人一直宣传的形象,但种种迹象表明真相并非如此,并且他的问题都很明显在报告中被忽略了。
警方发现的扎哈里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本应引起注意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但他们得出的正式结论却差强人意。官方报告中称扎哈里为PIC,即主驾驶(pilot in command)。报告里说:
据称PIC对工作压力的承受力很强。没有任何已知的冷漠、焦虑或易怒史。他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也不存在人际冲突或是家庭压力……没有行为迹象显示社交孤立或是兴趣爱好的改变……根据PIC在航班飞行当天和此前的3次航班监控录下的行为模式,没有发现明显不同。在所有的监控录像中,他和往常一样外表光鲜,衣着整齐。步态、姿势、面部表情和言谈举止都符合他的正常个性。
扎哈里似乎和他早期稳定的生活脱节了。他和自己的孩子还保持联系,但他们已经长大离家了。对人生的倦意与孤独经常与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相伴,而扎哈里正是社交媒体重度使用者,这很可能对他有害无益。航空业和情报部门的调查人员强烈怀疑他在临床上属于抑郁症。
扎哈里的飞行模拟器进行的法证调查显示,他模拟驾驶的一条航线剖面与马航370大致相符——即向北绕印度尼西亚,然后向南长途飞行,最终在印度洋上空耗尽燃料。马来西亚调查人员声称这条模拟航线只不过是模拟器记录的数百条之一。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这只是表面。独立调查小组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弗吉尼亚州罗诺克的工程师兼企业家维克托·伊南诺(Victor Iannello)对模拟飞行进行了大量分析。他特意强调了马来西亚调查人员的遗漏之处:从模拟器中提取的所有剖面中,唯一与马航370飞行路径匹配的剖面,也是扎哈里唯一没有进行连续飞行(在模拟器上起飞,一直持续飞行直到抵达目的地机场)的剖面。与之相反,他手动尝试了飞行的多个不同阶段,不断向前快进,并在必要时减少燃料,直到燃料耗尽。伊南诺认为这是扎哈里有意凸显这次模拟。在这款游戏机似的微软消费产品上进行预演,扎哈里 并不能在技术上学到任何新东西。因此伊南诺猜测,扎哈里进行这次模拟飞行的目的可能是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与世界道别。伊南诺谈到马航370可能就是按这个航线飞行的。他这样评价扎哈里:“他好像是在模拟一场模拟飞行。”扎哈里没有留下任何解释,他的动机无从得知。但这条模拟飞行轨迹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巧合。
扎哈里的一位终身好友,也是一位波音777客机的机长。考虑到可能对他造成的影响,这里隐去他的名字。他也认为罪责在扎哈里,尽管他并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把这一神秘事件描述成一个底部很宽但顶部只容一人的金字塔,意思是调查开始时会有很多推测,但最终解释只有一种。他说:“这说不通。这和我认识的那个人并不相符。但这是唯一合理的结论。” 我提到扎哈里还得对付驾驶舱的同伴、副机长法里克· 哈米德。他回答:“这很简单。扎哈里是教练。他只需要说‘去检查下机舱’就好了,然后法里克· 哈米德就会离开。”我询问他动机。他不知道。他说:“扎哈里的婚姻很糟糕。他之前和一些空姐睡过。但这有什么?大家都这样做。你满世界飞,身后就是这些漂亮女孩。但他妻子知道了。”他也同意这几乎不是丧失理智的原因,但他认为扎哈里的心理状态可能是一个因素。
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在官方报告中——扎哈里的痛苦、模拟器上特殊的飞行剖面——更不用说报告本身的技术性缺陷了,这些是否都说明有人在试图掩盖真相?目前我们无法确认。我们知道了调查人员知晓却选择不公开的有些东西。可能还有更多他们发现了却不让我们知道的东西。
让我们回到马航370航班的消亡。不难想象扎哈里的最后时刻:他束着安全带坐在超舒适的驾驶座位上,沐浴在熟悉的仪器闪烁的光亮中,就像把自己包裹在茧体里,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也不用赶时间。他应该早就给飞机重新加过压,调节好了温度。这里有机器运行的嗡鸣,平板显示屏上着的是抽象而美丽的画面,还有开关和断路器发出贴心的背光。空气在耳边轻声流动。驾驶舱是最深邃、最安全、最私密的家。早上七点左右,太阳从飞机左侧的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几分钟后,它照亮了飞机下方的海面。这时扎哈里已经死去了吗?他有可能已经在某个时刻再次给飞机减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存在争议,并非确定无疑。没错,根据调查人员对燃油耗尽状态的模拟,如果飞机无人控制,并不会像卫星数据展现的那样以极端姿态坠入大海——换句话说,很可能是最终有人在控制,帮助飞机坠毁。无论扎哈里当时是生是死,在第七弧的某处,引擎因为缺乏燃料而失灵后,飞机进入了剧烈的螺旋形加速坠落,最终速度可能超过了每分钟1.5万英尺。根据飞机的下降速度,以及布莱恩·吉布森找到的碎片,我们可以知道飞机在坠入水中时分解成了碎屑。
7. 真相
法国人也只是在国内重新分析卫星数据。马来西亚人则希望整个话题都不要再被提起。去年秋天,我在马来西亚的行政中心布城参加了一场活动,格雷斯·内森、吉布森和交通部长陆兆福(Anthony Loke)一起站在镜头前。部长正式接收了在夏天收集到的5块新残骸碎片。
内森希望海洋无限公司能够再一次在无结果不收费的条件下继续搜寻工作;该公司最近找到了一艘失踪的阿根廷潜艇。那周初该公司暗示这并不是没有可能。但马来西亚政府必须签署合同。根据对马来西亚的了解,内森担心他们不会愿意签这个合同——到目前为止,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除此以外,找到飞机残骸和两个黑匣子可能没有什么用。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只有两小时的存量并会自动循环消除,很可能只会录有最后警报响起的声音,除非当时控制飞机的人还活着而且还有心情为历史留下解释。另一个黑匣子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它能提供航班在整个飞行过程中运行的信息,但不会提供任何相关的系统故障信息,因为没有任何故障能够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飞行数据记录仪充其量只能回答一些相对不重要的问题,比如飞机是在何时失压的,以及失压持续了多久,或是卫星通讯箱如何断电后又重新恢复供电的。网上那些拒绝正视现实的人们可能会对此着迷,但这可不是什么值得期待的事。
最有价值的答案很可能并不在海洋里,而是在陆地上,在马来西亚。这才应该是今后的关注点。答案可能近在咫尺,但它们比任何一个黑匣子都更难找回。如果布莱恩·吉布森想来一次真正的冒险,他可以考虑在吉隆坡待上一年,搜寻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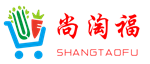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