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无法通过一个人现在的样子,知道他内心的往事。
那是2006年,38岁的马东没有了父亲。
父亲去世几年之后,马东做了一个梦,梦里,父亲对他说:我今天才真正走了,很高兴和你做一世父子,有缘再聚。
2012年,44岁的马东辞去了在央视的工作。高歌猛进的事业,解决不了生命中的太多疑惑。每个人,都要作出某种选择。
央视管理层、两届春晚导演、知名栏目主持人……这些,他都不要了。
后来,《奇葩说》《乐队的夏天》《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让他爆红于流量,也受困于流量——他应该对这些早已有了免疫,毕竟,他已亲眼见过父亲掌声雷动的华年,也见过他落寞无措的晚年。
2006年过去了,他一定,很想他。
新的一年开始了,一个人的道路,只能自己走下去。
至于是迎来掌声还是嘘声,那都将成为岁月里的花絮。


制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档节目,并不是马东的本意。
那是2020年的秋天,米未公司制作的一档音乐综艺刚刚送走了炙热的夏天,米未的几个合伙人坐在一起,讨论接下来要做的综艺类型。
有人支持接着做音乐,趁热打铁,再创辉煌——这也是马东的选择,但也有人话锋一转,想挑战一个新的领域:喜剧。
毕竟,公司里坐着这么一个“喜剧大师之子”,也是有这个底气的。
说服马东的过程十分简单。
合伙人内部举行了一场“辩论赛”,各自观点的人自发地形成团队,摆事实、讲道理,谁把对方辩到哑口无言,谁就赢了——作为公司创始人的马东,坚定地选择了音乐。
而结果是,经过了9个月的筹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播出了。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片头
这可以说是2021年年末,最具讨论度的综艺节目。
没有专业限制,更少见煽情戏码,马东上来就对参加比赛的演员们说:“只要你能获得观众掌声,你爱干嘛干嘛。”
于是,在那个世界即将变得金黄的秋天,喜剧的春天反而来了。
不同于大众熟知的相声、小品,这个节目告诉观众:喜剧可以是任何形式。
比如,第一个引起关注度的作品《互联网体检》,是一个Sketch(素描喜剧),就是将一个笑点不断升级的玩法。
扫脸识别之后个人信息一览无余,大数据时代没有秘密;正式体检之前得先看一段广告,想要跳过广告就得开通会员;抽血的时候只扎不抽,想要完整的抽血体验需要下载APP……精准拿捏了被各种APP的隐藏消费激怒的网友。
此外,还有音乐剧、漫才、小丑戏,甚至,就是单纯的、毫无意义的好笑。

第一季作品《父亲的葬礼》
马东在节目中说,“喜剧是一面镜子”。在日后的采访中,他也强调,“照见时代生活的某一个侧面,让观众可以从中释放焦虑情绪、思索一些命题,喜剧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
在乱麻一般的生活中,很多人把喜剧当成酒在喝。
在这样的语境加持下,足够好笑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获得了成功。
那段时间,网友们将马东在比赛中的点评金句截图传播,感慨他对于综艺制作的辛辣眼光,铺天盖地的舆论走向是:不愧是马东。
就连李诞也在节目中直言:“米未是我的大学。”

一年之后,第二季的大幕拉开,观众们早就被吊足了胃口。只是,众口难调。
在豆瓣上,仅仅有57%的观众给出了好评,长评区更是挤满了长篇阔论,指责它“失去了初心”。相比于第一季93%的好评率,马东的综艺光环,似乎失灵了。
但跳脱出数据来看,这档节目是否真的没有可取之处呢?
时间回到2019年的夏天,这也是属于乐队的夏天。
《乐队的夏天》总决赛的那一晚,有两个姑娘坐在观众席,看着舞台上绚烂的烟花,眼睛里全是羡慕。刘胜瑛问旁边的金靖:“即兴喜剧的夏天,什么时候可以来?”
金靖的回答是:“可能永远都不会来了。”

彼时,刘胜瑛正被迫转向喜剧的幕后工作,找不到露脸的机会,金靖好一些,却也摆脱不了“综艺咖”的标签。
直到一年之后,她们等到了“喜剧大赛”。
在第一季中大放光彩的蒋龙,曾也只是个“腰部演员”,最知名的代表作,是豆瓣评分2.2分的《逐梦演艺圈》。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他已经在考虑转行。
到了第二季,新面孔的比例依旧没变。
最出圈的“少爷和我”组合中,主演鑫仔曾在第一季的淘汰赛中就被淘汰;擅长“独角戏”的演员李逗逗曾做过群演、上过《奇葩说》,为了生存,在北京搬了十多次家,最终,他们走向了这个舞台。

第一季选手 蒋龙
在第一季决赛中,马东将业内知名的制作、出品等公司的代表请到了节目现场,为台上的演员与编剧们,安排了一次特殊的“面试”。
编剧六兽创作的多个作品被称赞,收到了坏猴子影业递来的橄榄枝,邀请他参与电影创作;柠萌影业的陈菲更是直接在现场向演员王皓与史策递出了电视剧《二十不惑2》的合作合同。
正午阳光的董事长侯鸿亮说:“我看过的综艺不多,但我发现我看过的综艺,基本上都是马东做的。”
这种驾轻就熟的综艺效果与骨子里悄无声息的理想主义,被马东归功于:遗传。

第二季结尾换成了“导师的一句承诺”

在马东的记忆中,父亲马季很少会有笑脸——与他在公众面前幽默风趣的形象截然不同。
温情与宠溺,似乎很少出现在这对父子之间。
1968年,恰是马季人生中最难的一段岁月。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扣上了帽子,每天最忙的就是挨批、挨斗。
万般无奈之下,马季的妻子回到了老家哈尔滨待产,生下的儿子就是马东。再之后,马东一直被寄养在别人家中,直到长到三岁半,父亲才把他接回了家。
彼时,马东看着出现在眼前的陌生人,喊出口的第一句,是“叔叔好”。

马季与儿时马东
总有人会问马东,小的时候有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享受过什么特权,马东的回答永远都是:“有一个,这个特权就是你爸很忙,没功夫搭理你。”
小学五年,父亲从来没有给他开过一次家长会,只在马东闯祸后,被老师请过一次家长——这段唯一的经历被马东称为“有可能是我的小学老师想见我父亲一面,所以我爸才去的”。
这也是父亲唯一一次打他,当着老师的面,给了马东一记耳光。
彼时,马东在育民小学上学,学校里一大半都是广电员工的子女,几乎全学校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马季之子”。
因此,马东时常被高年级的学生“劫持”,架着他的脖子,拐到砖垛后面,逼着他说上一段相声——他并不会说,最后要百般求饶,才会被“释放”。

马东与父亲
尽管不曾学过相声,在耳濡目染之下,马东对相声也算得上精通。
他会背传统的相声小段,还能读懂相声文本的结构与效果,但他也知道,父亲并不喜欢他与相声产生关联。
父亲会在马东听相声的时候,赶他回房间写作业,也会在饭桌上,突然对儿子说:“长大以后干点别的,别说相声,没出息。”
马东也始终,不被允许去到后台,观看父亲的演出。
父亲一次次推他远离自己的行当,但现实是,在旁人眼中,相声大师的光环却始终扣在马东的头上。
小男孩心气高,为了摘下这个“星二代”的帽子,马东索性选择了离开。

马东与父母
1986年,18岁的马东,花了三万元人民币——父亲的全部积蓄,去到了澳洲留学。
出了机场,面前是高楼大厦的悉尼与时髦靓丽的外国人,马东穿着牛仔裤与皮鞋,搭配得不伦不类,他形容自己当时就是“聋子、瞎子和哑巴”,与这个外表光鲜的国家格格不入。
他在澳洲待了八年,为了让自己活下去,他几乎打过所有的工。
早上去做清洁工,然后去上学,晚上去餐厅打工,假期的时候,还要去揉皮子——袋鼠睾丸袋,这是制作澳洲传统零钱包的材料。
他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手感,“毛绒绒的,不是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就像是他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生,“舒适”一词与他毫无关联。

马东与父亲
1993年,马东25岁,父亲马季来到澳洲参加春节华人演出。
彼时,马东已经七年没有见过父亲了,他特意请了假,跟着父亲到处赶场演出,跑了好几个城市。
他看到了商场的光鲜、霓虹的闪耀,与往常自己生活的澳洲全然不同。也是在这个时刻,他坐在台下看着父亲的演出,突然觉得,父亲的相声竟然这么好看。
他知道,是时候回国了。

在澳洲留学期间,马东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科技公司上了几年班。
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会去唐人街租录像带,偶然之间,看到了一张光碟:中国台湾的主持人胡瓜主持的《金曲龙虎榜》。
马东眼前一亮,新世界的大门猛地打开:“原来这样也可以混饭吃,这也是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我好像也能做到。”
未来,仿佛就在这不经意间,拐了个弯。

马东旧照
回国之后,马东并没有找到直接转行的机会,于是去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念书,这次,他学的是电视专业。
上学期间,他开始跟着各个电视剧组实习,毕业之后还开了一段时间的广告公司,每天通宵打麻将,晨昏颠倒,睡到下午起床。
碌碌无为的日子过多了,马东自己也觉得没劲,干脆报名了支教,准备去贫困山区做贡献去。
恰在此时,一个机会触到了他的眼前。
1998年,湖南电视台筹办了一个叫《聚义堂》的综艺节目,需要一个男主持人,在朋友的推荐下,30岁的马东拿起了话筒。
但与想象中的游刃有余不同,马东站在舞台上手足无措,被台下的导演大骂:“这人是个棒槌”。
马东很沮丧,觉得自己或许不是个干主持的料。
当时是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最火的时候,湖南卫视也想制作一档谈话节目,马东嗅到了这个机会。他给节目的制片人写了一封长信,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一员。
恰在此时,在湘西溆浦,有9个结拜的混混,合伙抚养了一个被丢到街上的女婴,人生因此而改变,故事极具话题讨论度。
马东找到了这几个人,进行了采访,想要探讨话题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属性,《有话好说》的第一期录制,就这样开始了。
这档节目做了83期,每周播出一期,整整播了一年半的时间,直到,他触到了一条线。

《有话好说》节目组 马东(左二)
事情的起因要回到三年前。1997年,一部名为《他他她她的故事》的描述同性恋群体的小说集在中国香港出版,第二年,“认识同性恋”这一话题开始持续发酵,彼时,同性恋还被社会普遍认为是一种病。
2000年,马东邀请了两位同性恋者以及学者李银河一起,在《有话好说》的节目现场,与观众一起探讨对同性恋群体的认知。
风波从台下的观众席开始,在节目录制期间,就有观众高喊“恶心”,担心“节目播出之后,全社会都搞同性恋去了”。
马东却在节目最后总结道:“我觉得在一个健康和开放的社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事情,它明明是客观存在,却有必要大家都对它视而不见的。”
于是,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有话好说》也戛然而止。

《有话好说》的最后一期节目
马东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那一年,32岁的马东当着节目组制作团队的面掉了眼泪,“当时就年轻,觉得我又没做错什么,这是一种直路,为什么必须要弯掉?”
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与现实较劲。
几年之后,同样的剧情在他之后制作的节目中接连上演,仅《奇葩说》就有多期内容因为题材敏感而下架,而此时的马东却已换了说辞:“天下没有无边的舞台,你找到舞台的边界这样才最好,因为你这样更安全,你省得跳到舞台下面去。”
当然,这是后话了。

马东(左)旧照
2001年,深受打击的马东,离开了湖南台,回到了北京。
恰好《挑战主持人》需要一个补位的主持人,邀请递到了马东手上。但节目刚录了四期,马东受不了了,他找到了负责人金越,说自己真的干不了综艺了。
金越回复他:“我就是要击碎你,有什么不能干的?”马东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渐渐地,却也开始做得有模有样。

马东在《挑战主持人》
2004年,央视的新栏目《文化访谈录》公开招聘制片人,马东赢得了这个机会。
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档文化类的访谈节目,但比节目本身更有话题度的故事是,马东在节目中,旗帜鲜明地“怼”了做客的嘉宾——彼时正红得发紫的畅销书作家,22岁的郭敬明。
“如何解释《梦里花落知多少》与庄羽创作的《圈里圈外》有这么多巧合呢?”
“你觉得在文学上,尤其是在你这个年纪的文学创作上,是不是可以容忍借鉴和模仿?”
现场的气氛随着马东的提问越发紧张,郭敬明最后情绪失控,暂离了现场。
虽说如今郭敬明的抄袭早已盖章定论,但在该期节目录制的2005年,场下坐满了郭敬明的粉丝。如今,原版的视频已经在全网下架,但当年的一则报道描述了当时的现场情况:
“除少数观众对两书相似的问题继续追问外,许多观众表达了对郭的倾慕,表示‘郭敬明抄得这么好,又这样畅销,说明他有才华’。当马东询问有多少观众认同这种观点时,现场大部分学生观众举起了手。”
但马东没有退缩,“如果一个重大话题需要媒体表达立场、发出声音,任何一个媒体都不会考虑批评是否会得罪人。”

《文化访谈录》做出起色之后,马东有了一个新的念头。
他想以自己的职业身份与父亲来一次正式的对话,也是想向父亲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
2005年,马东逼着自己,去邀请了父亲马季,做客自己的新节目。
父亲听完,犹豫了很久,一方面,儿子很少求他,尤其又是工作的事情;另一方面,他或许也确实想看看儿子在工作上的表现。
最后,在《文化访谈录》的现场,父子俩并肩坐了下来,畅聊“关于相声传播方式的改革”。
节目播出之后,许多节目向两个人抛来了邀约,力争两个人再次同台。但父子俩无一例外,选择了拒绝,“这是我们两个人的默契,尽量不在一个舞台上出现,让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分得开一点”。
但彼时的马东或许没有想到,更大的分别,就在不远的将来。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肯白发向人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马季渐渐淡出了艺术舞台,在家中,有时偶然地路过了镜子,他还会被镜子中的自己吓一跳。
他看着镜子中的马季,头发花白,老态龙钟,记忆中那个鲜衣怒马、嬉笑怒骂的相声大师,在脑海中的印象不断淡去。
“一个演员老了以后,不愿意看自己的样子。他不愿意上台,尤其是不愿意上电视,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看见他老了以后的样子。”马东说。

马季(中间白衣服)早年在餐车上给人演出
但不上舞台了,不代表马季就闲下来了。他曾在采访中用“十六字箴言”描述自己的晚年生活——
以玩为主,玩中找钱,玩钱结合,有钱就玩。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邀请他,马季就开始去各地游玩,与相声爱好者们一起研究相声本子,写了好多相声小段。

直到2006年,马季突然对儿子马东说:“我觉得我有点老了,我应该过一些不那么跑的老年生活了。”
两天之后,马东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你父亲不行了。”
挂了电话,马东立刻开车往家赶,一个小时的路程走过,他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脸上没有痛苦,只是安详的平静——这个表情记在马东的心里,记了许多年。
这一天是12月20日,马季离开了他热爱的人间,享年72岁。

在先生的追悼会上,近百名文艺界名人和数千群众自发来到现场为他送别,有人扯着条幅,有人怀抱鲜花,还有人,带着与马季先生生前的合照——
一位70岁的老人抱着怀里的照片和周围的人讲解:“当时拍照的时候,本来让马老站最中间,可他执意要我站中间,说我是大学老师,是最受尊敬的人。”
作为儿子的马东,只是静静地为父亲申请了一面党旗,覆盖在他的身上,他记得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是党的文艺工作者。
他觉得,父亲应该是喜欢这个送别的。

马季早年与工厂厨师合照
父亲去世之后,马东辞掉了《挑战主持人》的工作。
他害怕自己站在台上,周围人都要劝他“节哀”,他不自在,也不愿意听,“毕竟还是一个娱乐的节目”。
三年之后,马东做了一个梦,梦里是父亲那张熟悉的脸。父亲对他说:“我今天才真正走了,很高兴和你做一世父子,有缘再聚。”
再往后,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星二代”这个身份,他不再想着逃离、撇开,他认真地告诉记者:
“这不是困扰,而是幸运。”

马季(中间黑衣服)早期演出

经常有人问马东:“你们为什么不去买国外的版权作品?”
而马东的回答是,“为什么要去买版权?”
2012年,44岁的马东离开了央视。
彼时,他已经在央视做到了管理层,担任了两届春晚导演,所有人都觉得,他会在央视发光发热,直至退休,但马东说:“我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马东在央视时期
第二年,45岁的马东宣布加盟爱奇艺,担任首席内容官一职。
进入网络平台,被马东形容为自己是在一辆高速列车上,扒着栏杆,在底下狂奔,“有太多我不懂,但我确实想要知道的东西”。
当时的同事也曾对外展示过这个局促的马东。
同事说,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老人家”,不愿意和他说话,马东就会主动来凑近乎,接水的时候也来聊天,玩游戏的时候也要掺和一脚。
他十分喜欢与年轻人混在一起,哪怕听到的都是年轻人对他的嫌弃,“每天被他们讽刺,是一种特别贱兮兮的快感”。

一天,马东与高晓松在一次聚餐中喝醉了酒,因为一件事争论不休,高晓松突然感慨:“哎,像咱们这样的‘大喷子’弄一个辩论节目挺好的。”
马东猛然意识到,为什么不可以呢?
“主流媒体传递出来的声音与价值观必须是正能量。我们知道正能量是好的,但有时想的会与这些不太一样,我们还会有其他观点。我们想要表达的是真实的声音,而不只是一种。”马东当时的同事牟頔在之后的采访中补充道。
于是,他们决定制作一档辩论节目,目标人群就是活跃在互联网上的“泛90后”。
天南海北的“大喷子”被他们挑选出来,一档别出心裁的语言类节目由此产生,这就是《奇葩说》。

马东在《奇葩说》中
《奇葩说》的成功,可以说是现象级的。
从2014年11月底上线之后,这档节目走过了七季,谈论了无数个话题,涉及到社会、两性、伦理、职场等等方面,引人发笑,也诱人深思。
而在《奇葩说》中,马东的作用至关重要。
因这个节目走红的肖骁就曾说:“这节目没变成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最大的功臣是马老师。”
他讲着荤段子,敲着小木鱼,像一根定海神针,见招拆招,将节目效果处理得圆滑且有趣。但在某些时刻,你又能看到他骨子里的温良。
罗振宇说:“脏话是人的情绪到了尽头。”马东却说:“人的情绪到了尽头是沉默。”
柏邦妮在节目中感慨:“心里全是苦的人,要多少甜才能填满啊?”马东却告诉她:“邦妮,你错了,心里有很多苦的人,只要一丝甜就能填满。”
轻巧之间,就能窥见他的本事,也似乎,可以看见他被深藏着的,理想主义。
“你(在社会上)看到了很多荒诞和不合理,那有没有合理的解法,或者仅仅是探讨,这个荒诞是怎么来的。”
尽管,他对外的说辞始终是:我就是想做一个综艺节目。

马东在《奇葩说》中
2019年,马东推出了新的节目,《乐队的夏天》。
事后他在采访中回应过节目的出发点,“我觉得对于所有已知的和存在的东西,都应该重新提出置疑和问号,这东西叫摇滚精神吧,或者是摇滚精神的一种吧。”
于是,他想要去看一眼乐队的生活,哪怕,他先天五音不全,对音乐一窍不通。

在这档节目中,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权威被挑战,只是作为一个入门者,大摇大摆地抛出一些最基础的疑问——就像是大部分的节目观众,去体会乐队与生俱来的传染力。
马东感受到乐队的魅力,就意味着观众也会喜欢上这个节目,进而喜欢上表演的乐队,这就是他的作用所在。
“你让我回想说,《乐队的夏天》的调性到底是什么,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但马东随后又提起了一个画面。
那是在《乐队的夏天》第一季的现场,刺猬乐队唱了一首歌:《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这是乐队在解散的飘摇时刻,由主唱赵子健创作的一首歌曲,他在舞台上撕心裂肺地唱:“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谁知,弹着弹着,吉他出了问题,最后,他气得将手中的吉他,砸向了身旁的架子鼓。
马东回忆起那个瞬间,他说:“在这一刻,我感觉这个节目内在的东西出来了,矫情一点说,就是真实的力量。”
《乐队的夏天》成为了那个夏天最火爆的综艺,节目的总制片人兴奋地说:“我真正开心的地方不是赚大钱,而是让乐队的生态变好一些,很多人现在知道live house了,知道除了电影院我们还能去那里。”
前后的对比是鲜明的。
刺猬乐队的主唱赵子健曾多次谈起自己的程序员本职,因为音乐节的收入入不敷出,他不得不坚持工作——后来,为了参加这档节目,在工作与梦想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辞职。
Click#15单靠乐队的收入1个月也只1000来块钱,连打车费都要和节目组抠抠索索地计较。而第一季的黑马乐队九连真人在参加比赛之前,还都是县城里的小学教师,贝斯是借来的,鼓手是临时请的。
最终,他们都在这个夏天,闪起了光。很多观众在这个夏天才意识到,原来中国的摇滚,始终没有停止沸腾。

在2017年的一次访谈中,许知远曾问马东,你喜欢这个新时代吗?
“喜欢。”马东非常坚定地说了三遍。
许知远接着追问他为什么,马东的眼睛转了几圈,吐出一句:“我没那么自恋”。哄堂大笑。
这场访谈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位文人与一位商人的价值观冲突。
许知远问马东,有没有感到娱乐节目有很明显的粗鄙化的倾向,而马东的回答是:“我们精致过吗?”
在马东的观点中,这个世界大约只有5%的人有积累知识的愿望,剩下95%的人就是在生活,而娱乐是人的先天本能。
“我们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在墙上画画。难道是为了名垂青史?它就是有趣,它就是娱乐自己。”
娱乐是粗鄙的,精致的是文化,文化是古代仅占少数比例的知识分子们沉淀下来的结果。
马东目前只想让这95%的人快乐,至于会不会形成一种文化,要等到历史来评说。

这档对话曾引起过轩然大波,在许知远这个书店老板的衬托下,马东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世俗的标签。
有节目因此讥讽他是“犬儒主义”,断章取义地认为他在阻隔这95%的普通人向往精致的路,是彻头彻尾的、利己的、虚伪的商人。
马东从头至尾,没有任何回应——“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在这档节目中,马东罕见地再次提到了父亲。
许知远问他:如果您父亲看到《奇葩说》,他会有什么感觉?
马东想了一下,说:“他应该不会喜欢吧,他会觉得有点闹。”然后,他模仿父亲的语气,笑着说:
“你们在语言当中夹杂的烈度这么大,真的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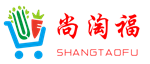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