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西域,埋藏着古丝路沿线璀璨的文明,在如今依旧惊艳着世界。
然而,记载着这些古老文化的西域古文字,在国内却曾濒临失传,全世界仅有少数学者才能解读。
1974年,几个工人在新疆七个星千佛洞挖出了几卷残破的神秘卷宗,上面的文字模糊又陌生,不仔细看就像是画符一样。
谁能破译这些卷宗?
博物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宣告失败,残卷被搁置,一直到1981年。
他们终于能带着卷宗去寻访国内唯一有可能破译这些卷宗的古典语言专家,当时已经70多岁的季羡林。
年逾古稀的季羡林戴上眼镜,细细端详这些顺序杂乱、字迹不清的残卷,惊喜地发现这是自己曾经得心应手的吐火罗文。
在当时,全世界能够掌握这门语言的学者屈指可数,季羡林正是其中之一,也是全国唯一。
历时17年,天书重现于世,全世界震惊于中国的古典语言研究成就,也震撼于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居然独立完成了这项举世瞩目的工作。
然而,面对名利和赞誉,季羡林并不在意,只挥了挥手:
“桂冠一摘,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
还是那么真性情,自由又洒脱。
01
“最穷的地方里,最穷的人家”
“考大学,不过为了抢个能够吃饭的铁饭碗。”季羡林在自己的日记里实诚地写道。
不同于很多有着家学渊源的民国大师,季羡林不论是求学还是和古典语言结缘,都充满了偶然性。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官庄的一个农民家庭。家里一贫如洗,是最穷的村里最穷的人家。
穷到什么程度呢?
一年到头,季羡林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家里没钱买盐,他只能想办法把盐碱地里的土扫起来,放在锅里煮水,腌上咸菜,当做日常的调味料。
至于读书,就更难想象了。他买不起书本,整个家里都找不出一张带字的纸,更别说送去私塾读书。
不出意外的话,季羡林会继续和村里的青少年一样,长大成人,种地挣钱。
幸运的是,他父亲的亲兄弟们当时都没有儿子,其中有个在济南的叔叔,家庭条件较好,于是季羡林的父亲就跟弟弟说好了,让儿子去城里投奔他。
从贫穷的小乡村到省城,季羡林的人生出现了第一个转折,他得以念书识字,还一路读上中学。
不过,那时候的季羡林还不知道古典语言是什么东西,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和它们紧密联系到一起。

年轻时的季羡林
十几岁的季羡林应付着学校功课,成绩排在中游,还是个偏科学生——
他平时最喜欢看《水浒传》《金瓶梅》等话本小说,还在课外学英语,所以这两科总是读得很好。至于数学,则学得很一般。
结果没料到,这样的“不务正业”却让他进了清华的大门。
高中时,季羡林非常自信,只填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
恰好当时北大加试了英语听写,许多没怎么学过英语的考生纷纷落榜,季羡林却轻松通过。报考清华时也是如此顺利,虽然他的数学卷子几乎写不出来,但他的国文和英文脱颖而出,吸引了判卷的先生们,让两所高等学府都对他伸出了橄榄枝。
成绩出来后,季羡林在学校一时风头无两。

年轻时的季羡林
他为了争取留学机会而选择了清华大学,进入西洋文学系,就此与他钟爱的语言文学难解难分。
他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一生的乐趣,并为之努力。
哪怕那时候,就算是清华毕业的人文社科学生也难有出路。
哪怕这种专业,多半是清贫半生,与钱无缘。
但少年意气,季羡林不管这些流言蜚语,只是从心而行。
02
寻找一生志业
在当代,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文化与文物瑰宝不断被挖掘、解读,带给人无限震撼。
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珍贵稀有的经卷却被误认为是废纸,转手流落到国外,成为国外博物馆、图书馆的藏品。
而有些侥幸存留的材料,也因为国内几乎无人能够解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学的外文系,学的都是广泛应用的语种,就连清华和北大也是如此。
季羡林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主修的是德文,课程照本宣科,十分教条和应试,让他不厌其烦: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能让他提起兴趣,认认真真去听的,估计只有陈寅恪和朱光潜的课。也正是这两门课,让他真正对自己未来钻研一生的古典语言产生兴趣。
陈寅恪在历史系讲“佛经翻译文学”,直接从佛经开始解读,在课上进行注解。上课的学生们,人手一本《六祖坛经》,一开始听得晕头转向,等到逐渐入门,方能明白其中奥妙。
季羡林就是如此。他听着精妙的佛理,手抄晦涩的经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拜读陈寅恪的论文,对古代中印文化充满了向往。
也因此,他在心中埋下了一颗想要学习梵语的种子,只待后来生根发芽。
毕业之后,季羡林先是在中学任教,在不同派系间摸爬滚打,被排挤到边缘。
终于有个机会,他能够重新去考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于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留学之路。
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寻一条出路。

季羡林从清华毕业
在德国,毕业困难,很多中国学生为了降低学业难度,会主动选择研究汉学相关的内容。
但季羡林对此不屑一顾,甚至抬杠似的给自己定下了三条学习准则:
“第一,要学古代曾经给人类带来过荣光的语言。
第二,要学中国很少或者没有人掌握的语言。
第三,不投机取巧,关于中文的题目,一概不做。”
尝试过古希腊语、古埃及语等语言之后,他决定主修印度学,尤其是要掌握梵语、巴利语等国内几乎无人能解读的语言。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Sanskrit(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

季羡林在德国
幸运的是,他在德国遇到了许多恩师。
比如,他的梵文课师从瓦尔德施密特。很长一段时间,季羡林天天到高斯-韦伯东方研究所上这堂只有他一个人听的课,老师也并不因为课上只有一个外国学生而有所保留,而是倾囊相授。
或许面对有志于传承绝学的学生,很多老师都是这样,恨不能将一生所学都交付给下一代传承人。
精通梵文的瓦尔德施密特是如此,掌握绝学吐火罗文的西克也是如此。
在他们眼中,没有中外之别,没有人种之分,也没有丝毫偏见。有的只是自己热爱一生的知识,以及一个和自己一样充满热忱的学生。
吐火罗文残卷仅在中国新疆才有出土过,原本,它在这个世界上早就失传,是西克和西克灵在比较语言学家舒尔策的帮助下才破译出来的。
而当西克垂垂老矣,他的夙愿便是将他和挚友抢救出来的语言,教授给愿意传承并继续研究的学生。

季羡林在哥廷根
在德国的那十年,季羡林和老师们一起,埋头钻研古典语言。
有时候炮火轰炸,刚好到他们的街区,就连窗户玻璃都被震碎了,他们也只是稍微清扫一下,又继续伏案研究。
跟随着老师的脚步,季羡林在德国的古典语言研究之路已经卓有成就,本能够在国外知名大学担任教职。在战争结束、能够归国的时候,他却决定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
为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女。
更为了自己在异国他乡朴素的愿望:
回到中国研究古典语言,假若国内没有传承,那他愿意做那个带来火种的人。
03
继往圣之绝学
季羡林最不后悔的事情,或许是,不管何时,他都没有停止过写作。
尽管他戏称自己“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差不多就是文不如司书生,武不如救火兵”,可他依然笔耕不辍。
回国之后,在恩师的推荐下,季羡林得以在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后担任系主任。
工作稳定,经济独立,看似一切步入正轨。
然而,远在海外图书馆的西域古典语言资料和残卷难以获得,他想继续进行纯粹的语言研究就像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几乎是不可能的。
按季羡林从前的学术成就,接下来哪怕是就此躺平吃老本,也毫无问题,但他显然不是这么一个愿意混混资历、水水论文的闲人。
没有专门用来研究古典语言的一手资料,他就发挥国内资料的优势,研究起古代的中印文化史。
即将失传的语言在手,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倒也让他挖掘出了不少被人遗忘的资料,还大大推动了中印比较文学的发展。

有一回,胡适和知名历史学家陈垣对于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双方争论相持不下,又都是学界权威,各有道理。
季羡林本着做学问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
他用吐火罗文的知识去分析词根,写成了《浮屠与佛》这篇论文,并发表在当时的国内顶刊上,由此声名大振。
可惜,命运总是捉弄人,季羡林也没想到,他会差点与学术无缘。
据说后来季羡林的梵文恩师瓦尔德施密特访华时,他将自己在动荡时期翻译的梵文《罗摩衍那》送给老师,老师非但没有自豪,反倒是恨铁不成钢地问:
“难道我教给你的,就是这些吗?”
瓦尔德施密特想象不到,这样一部在语言学大师看起来堪称“小技”的翻译作品,实则来之不易。
他的得意门生季羡林在那些年里,书被烧了,书桌被砸了,连时间也被挤满了看门、打扫卫生、接收电话等杂务。
季羡林只能在黑灯瞎火的短暂休息时间里,躲开所有人,才能够一字一句地完成这部300万字的译著,搭建起中印文化的桥梁。
这种与时间赛跑的习惯,在平反之后依然牢牢刻印在季羡林的生活中,催促着他前进。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不曾忘记自己对待古典语言的初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季羡林得以重拾搁置了几十年的吐火罗文研究。
20世纪70年代,新疆出土了用吐火罗文A记载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当80年代新疆博物馆的负责人亲自上门请季羡林进行解读时,他原本因为自己多年没研究过吐火罗文而没有信心,想要推辞。
但在真正看到残卷、尝试翻译之后,他就知道——
这件事,他非做不可。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季羡林整理了这些乱序的残卷,根据回鹘文同书的译本把手头的吐火罗文经卷整理了一遍,陆陆续续用中英文翻译。
偶有不确定的地方,他请了两位国际上公认的吐火罗文权威学者帮忙补译了一两段,而其他98%的内容都由季羡林独立完成。
等到天书重现于世之时,他不无骄傲地说:
“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
这位置,是他拼着自己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挣过来的。
正如季羡林自己说的,甘坐十年冷板凳,文章不说一句空。五六十年来,不管是高峰还是低谷,都没能磨灭季羡林自少年起的那股韧劲。
也正是这样一种不被外力所摧折的韧劲,让他一次又一次创造了不可能的奇迹。
04
三辞桂冠
晚年的季羡林,写就《糖史》,破译《弥勒会见记剧本》,著作等身,享誉国内外。
而在无数的荣誉和名头之下,他从来不希望自己被奉上神坛。
据说,在白岩松采访时,季羡林曾说过自己当上北大副校长后发生的一件趣事。
有一个北大的新生,入学时因为行李太多,拜托路上一位面善的“老校工”帮忙看顾行李,自己先去办入学手续。
没想到,这一去,就因为排队等事情耽搁了一个早上。等到学生回去找行李的时候,却发现那个老人还站在阳光下帮他守着行李,没有离开。
他以为这只是一个热心的普通老人,直到开学典礼那天听到校长讲话,才发现,那个热心的老人竟然是副校长季羡林。
可见季羡林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平易近人。

季羡林和他的猫
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给季羡林的评奖词中写道: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
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这或许是旁人眼中,对于季羡林一生成就的一个总结。
但对于季羡林自己而言,他所愿的,或许只是探索未尽的知识,不为名利,不为赞誉。
因此,在大家为他加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称号时,季羡林专门写了文章出来推辞这些将人神化的荣誉称号,直言: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谦虚又实诚,他仿佛和几十年前在清华园日记里信笔直书的少年人一样直率,未曾改变。

晚年的季羡林依然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不买新房,也不换掉还没坏的家具。
一张摇摇晃晃的铁架床,一块塞了稻草的破床垫,几块旧得不能再旧的椅子,是季羡林家中不变的风景。
他仅有的财富,是自己收藏的书籍、字画以及一些古董,但这些,后来大部分都捐给了北大,来去无牵挂。
如今人们怀念季羡林,敬仰的不仅仅是他空前绝后的学术成就,更是他对待知识的那一份虔诚和坚守,以及对待生活的坦荡与云淡风轻。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不汲汲于名利,坚守自己的“道”,这或许也是像季羡林一样的前辈们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
1.季羡林 《季羡林自传:我的前半生》
2.季羡林 《留德十年》
3.季羡林 《清华园日记》
4.季羡林 《牛棚杂忆》
5.白岩松专访季羡林 《东方之子》
6.蔡德贵 《季羡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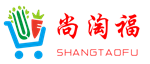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